本中心主任胡念祖特聘教授於海委會海洋保育署「海洋漫波」電子季刊第4期發表「臺灣與海洋國際組織之合作發展」
臺灣與海洋國際組織之合作發展
作者/胡念祖教授(國立中山大學特聘教授、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海洋事務研究所所長、政治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在開始探討本文主題之前,吾人必須要問一個「大哉之問」,那就是:一個主權國家為何要加入(accede to)一個政府間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GO)的設立協定(constitutive/constituent agreement),並因此而成為該組織的成員(Member),但同時卻得遵守(comply with)該設立協定之所有條款(provisions),盡條約之義務,還得繳交會費、遵守該組織所作出的所有決定(decisions)或規範(rules and/or regulations)?這樣豈不自我減損(undermine)國家主權及管轄權下的自由裁量(discretion)的權利與空間?
獲利大於損失
上述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直白,那就是:國家在加入IGO之後,必然獲得一些好處或利益,且在經國內諸多衡量後,覺得這些好處與利益比所失去的權利要多些。換言之,在追求自我利益極大化下,加入比不加入還要好,所以國家就會加入一個IGO。
用學術一點的語言來說,因為IGO是主權國家們藉由他們所共同議定之設立協定所組成,故一個IGO之設立必然服務或有助於該組織之組成國家們就某些特定目的之共同達成;而一個IGO之有效運作或功能發揮,亦有賴於其組成國家們共同遵從該設立協定之條款,以及遵守依該設立協定規定之程序所作出之種種決定(decisions)或訂定之種種措施(measures)。故,主權國家在依各自國家利益衡量與判斷後,自願加入IGO之設立協定,並成為該組織之成員時,必然在某種層面上減損其國家自主之權,但同時也換取一定之參與利益。
換言之,一個主權國家自願接受一個國際條約之約束,並遵守該條約所建構之國際(法律)秩序及一應措施,必然是符合該國家某種利益的追求。此種行為或許可以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Realism)來加以描述與解釋。亦即,在國際社會中,國家是最重要的行為者,國家之上則無其他行為者有能力可規範國家們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國家們自主地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用以追求自我利益與生存;或曰,國家在進行決策時,權力與利益的考量是高於理想或道德的訴求,而加入一個IGO也必然符合或滿足一個國家的利益。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與「自由建制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亦可描述與解釋國家自願加入IGO之行為。前者認為國家行為者自我的認知身分(identity)及利益(interests) 可藉分享之觀念(shared ideas)而得以建構;後者則認為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存在能夠增進國家間的合作。
國內治理與IGO密切相關
不論學術理論是如何描述或解釋國家行為,有一個事實的現象吾人必須面對,那就是在現今國際社會中,許多的國際規範均是由不同領域的各個IGO所作出。IGO的規範幾乎影響到每個國家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各種事務。譬如,海域所涉及之人安、船安與航安及海洋環境之保護的諸多規範係由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所作出。漁業及養殖活動之全球規範,係由聯合國糧農組織(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所作出等等。近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之作為更影響到全球人命之安危。IGO之規範緊密地影響或衝擊到每個國家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事務,使得「參與」(participate in)或正式「加入」IGO,變成國家在「國內治理」與「國際合作」上很重要的議題與事務。
探討本文的主題即應由上述「國內治理」與「國際合作」兩個面向觀之。
外交部官方網站顯示(註一),我國以正式會員地位加入的IGO共有38個,其中區域漁業管理組織(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即有6個,再加上「北太平洋鮪及似鮪物種國際科學委員會」這一個區域漁業科學組織,共有7個之多,佔了18.4%,將近1/5。這是因為我國善用了1995年聯合國魚群協定(註二)第1條第3項中所定義的「漁捕實體」(fishing entities)此一「非國家」(non-State)的法律身分(legal capacity),再加上我國遠洋捕撈實力,使得各大洋區的RFMO都有強大意願將我國納入各該RFMO之管理體制。如前所述,加入這些RFMO當然會使我國必須遵守各該RFMO或區域漁業科學組織之設立協定的條款及依該等條款所作出的種種漁業資源養護與管理措施(即遵約加上善盡條約之義務)。如此一來,這些國際規範就會進入我國國內的漁業法制與規範,而改變了我國國內在漁政管理或漁業治理上的內涵與樣貌。同時,我國亦透過這些國際組織,與其他締約國家們進行「國際合作」,以共同達成漁業資源養護與管理的目的。
加入海洋保育IGO
但,值得吾人注意的是,這38個IGO中,沒有一個是與海洋生物/生態保育、海洋環境保護相關的組織。換言之,作為一個已開發且國內有著強大環境意識的進步國家,我國卻未加入任何一個海洋保育政府間國際組織,這實在是一個極不相稱的情境與畫面。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大的落差,主要原因在於我政府某些機關只重視漁撈之「有形利得」(tangible benefits),卻把保育等視為必須「付出」的負擔。其實這是一種十分錯誤的認知與心態。
如果想在一個以保育為設立目的或宗旨的IGO中成為一個受到尊敬的成員,就必須展現出對該組織所涉保育標的與事務的專業度,而這種專業程度的高低,就涉及到「國內治理」面向所必須考量及做到的專業科研實力與人才的培養。譬如,欲參與及加入極區生物之保育組織,就必須有極區研究之能力,並對極區生物及其保育有一定的研究與瞭解。同樣地,欲參與及加入海洋哺乳類動物之保育組織,就必須有對海洋哺乳類動物及其生態與保育具研究實力的國內團隊存在,如此,亦會因該等國內科研實力的存在與提升,而提振國內鯨豚保育制度的發展與健全,也就貢獻了「國內治理」的工作。同時,藉著這些海洋保育IGO的平台,我國政府與專家學者們亦可充分地與其他國家政府與專業人士進行「國際合作」,以達成該等組織的設立目的。
積極參與 轉換利得
上述這些正向的反饋,其實也都是國家的「無形利得」(intangible benefits),而這些「無形利得」其實可以很快地轉換成為「有形利得」。譬如,因為對海洋生物物種保育工作與法律體制的深化,吾人獲得了更健康的海洋與棲地環境,進而獲得更多的漁獲或更大的海洋觀光遊憩產業的發展,更直接提升了相關產業從業者的經濟生活水準。
所以,在探討及看待台灣與海洋國際組織之合作發展一事上,吾人應該有更宏觀的視野及更高的政策高度,由 「國內治理」 與 「國際合作」兩個面向思考國家的利益,而非僅由「有形」之「金錢利得」的狹隘觀點出發,判斷國家利益的內涵。
作為一個海洋國家,我政府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藉由參與及加入海洋相關政府間國際組織以提升國內海洋治理之能量,以及藉海洋相關政府間組織的平台,以促進並強化國際合作,以達成全球海洋的永續發展。
(註一)外交部>外交資訊>參與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參與現況>正式會員,https://www.mofa.gov.tw/igo/News_igo_1.aspx?n=163B8937FBE0F186&sms=53182B822F41930C,上網檢視日期:2020年6月1日。
(註二)該協定之英文全名為"The United Nations Agre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簡稱為UN Fish Stocks Agreement。中文全名較精準之翻譯為「為履行1982年12月10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跨界魚群及高度洄游魚群養護與管理相關條款之聯合國協定」,簡稱為聯合國魚群協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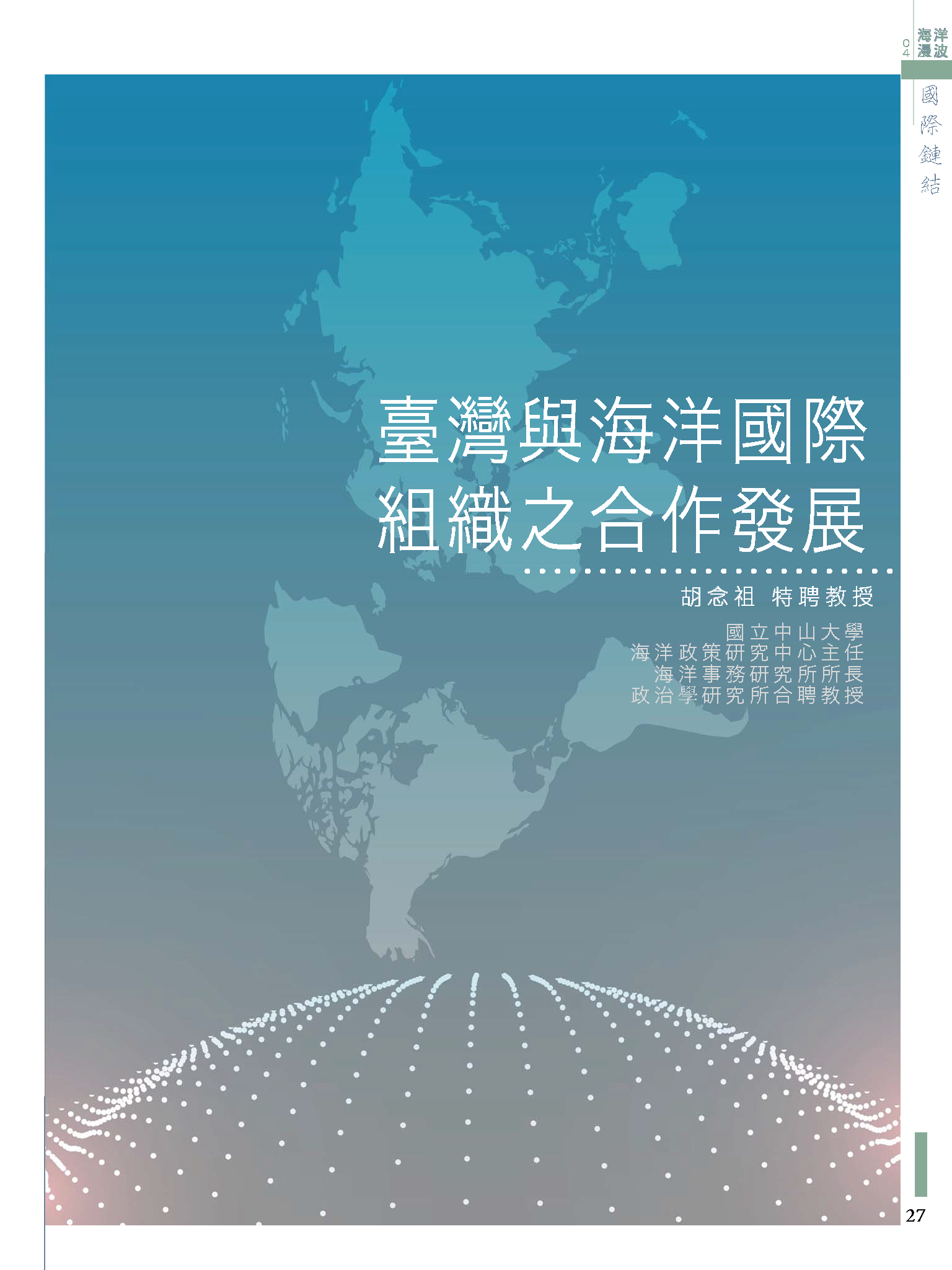
胡念祖,〈臺灣與海洋國際組織之合作發展〉,《海洋漫波》電子季刊,第4期(2020年6月30日),https://www.oca.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007010004,頁27-32。
